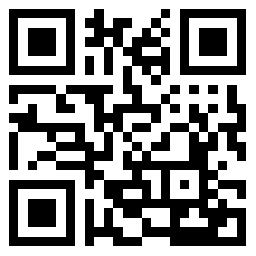

對沒有親眼目睹、沒有親身體會的人來說,它就是天方夜譚。
我是1999年開始涉及艾滋病研究這一領域的,當時,我在泰國國立馬希德大學留學。後來我在泰國做過艾滋病的熱線援助,說句不怕你們笑話的話,剛開始我對這個病還是有點恐慌的。
我自問並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當初做這個選擇,動機其實非常單純。艾滋病這個東西,在短期內,防也防不住,治也治不好,現在已經有上百萬的病源,未來十年裏甚至可能達到一千萬。我是高校裏的一名老師,當時關於艾滋病的研究,其他領域都已經有學者在做了,只有社會支持體系這一塊,是個空白,所以我選擇從這裏入手。這哪裏是理想主義呀?這是現實主義!
“北京昨晚來人了!”
2002年6月4日,我進村了。
我平時就不修邊幅,到了農村更加如此,高耀潔的老伴打趣我,說我像個農民。就是這副農民打扮,也根本瞞不了當地的村民。下鄉第二天的清早,村裏就開始傳言:北京來人了!昨天夜裏已經進駐本村!
當時,地方政府控制得還很緊,根本不讓外人進村,高耀潔、桂希恩那會兒都只能“打游擊”,有些香港的宗教機構、慈善組織募集了麪粉啊糧食啊,只能開着車經過,把東西扔下就跑。
我的待遇比他們稍好一些,我是帶着復旦的正式課題去的,而且“社會支持”這個課題,沒有什麼攻擊性,當地政府因此比較合作。不過,進村以前,他們還是跟我約法三章:一、當地只接受善意的幫助 ;二、任何報道,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當地來說都是負面的;三、不能打着當地的旗號去募捐。我答應了。
我們學醫的人,整天跟死亡打交道,神經應該都是很強韌的了,而且我這個人從來都不做夢,可那段時間,我連睡覺時,眼前都是亮晃晃的慘白一片。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衛生局長問我,“昨天看下來,有什麼感覺?”而我當時,已經連說話、連思維的力氣都沒有了。#p#副標題#e#
“死的你就不看啦?”
兩年來,我在河南和廣西兩個省實地調查,走訪了數十個村落,接觸了上千名患者,並對其中較爲典型的幾十例家庭作了訪談和記錄。先後訪談了60餘位感染者,約40位感染者的親友和20位知情人,包括各級基層幹部、醫療衛生人員等等。
我自己沒有什麼錢,如果說艾滋病救助的工作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話,我屬於“有力出力”的類型,不過,我把不少“有錢出錢”的人引到了疾病一線。
第一次進村的時候,我備了幾十個信封,每個信封裏是五十元錢和我的一張名片。因爲當時的抗艾情勢還很緊張,我怕我來了一次再也來不了第二次了,留下名片的話,以後病人還能找到我。
就這樣村裏很多人認識了我,不少人通過名片來找我,你看地上的這一包紅薯,就是幾天前一個村民來上海找我給我捎來的。
我愛人也挺有意思,我每次下鄉掏錢給病人,她免不了要埋怨幾句。但病人到了上海,她看到他們那個樣子,心腸一軟,又揹着我偷偷塞錢給他們。
在直面艾滋病的那些日子裏,我掉過一次眼淚。
是我第二次進村的時候,我遇到了以前訪談過的一位老媽媽,當時我正在她鄰居家訪談,她非要我再上她們家看看去,說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一邊翻曬麥子,一邊等我,我只好去了。這個老媽媽有四個兒子,全都是病人,老大、老二已經發病死了,留下媳婦、孩子。老媽媽的老伴七十多了,每天到公路邊上幫人裝砂,裝一車能掙五毛錢,一天累死累活也不過掙個七塊、八塊的,這一大家子人就指望着老爺子裝砂的幾塊錢過日子。我去的時候,他們家已經半個月沒有鹽吃了,而且從春節到麥收都沒有吃過一滴油!你絕對想不到,在當地,一兩油,都可以作爲媽媽送給女兒的珍貴禮物。
我看過他們家,留了點訪談費以後,老媽媽又求我,“你再到我的老大家去看看,好嗎?”因爲天色已晚,我當時很猶豫,老媽媽突然把手中的麥匾重重地一放,很大聲地說,“噢!活着的你就看,死了的你就不看啦?”
她一說這話,我們兩個都哭了。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個感情充沛的人,也許算吧。我平時很沉默,不愛說話,但到了自然的環境中,我的話就多起來,很活躍,像換了一個人。我從小生長在廣西的山水之間,至今沒有習慣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裏生活,苦悶的時候,我會騎着車子,去郊外,去山上,去海邊。進入艾滋這個領域以後,常常覺得心很累,實在無法承受,我會到海邊,想象着遠處的海面有一條小船,而我是船上的一個人。#p#副標題#e#
“這個錢,該由政府來給”
訪談裏最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死了,你的孩子怎麼辦?”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出口,我只好拐彎抹角地、用盡可能委婉的方式來問。對這些苦命的人來說,他們前面的路,幾乎都是堵死的,他們想不到將來。
死了的已經死了,沒死的就在那裏撐着,許多人已經認命,惟一割捨不下的就是孩子,你不把他的孩子安置好照顧好,他活着的時候就可能爲了他的孩子,去偷、去搶、去坑蒙拐騙。
有一個村子,村口住着一個老母親和他的獨養兒子,兒子染病。我常常看到老媽媽在村口曬茅草——做飯的時候用來生火的,城裏人看了一定會很奇怪,會覺得她是在曬垃圾,這個東西也當個寶翻來覆去地曬嗎?那天我去她家,她兒子已經臥病在牀,搖搖晃晃地起來接受我的訪問,我一看他們家特別困難,就提前把訪談費拿了出來,村醫很反對我這樣做,因爲錢提前給了,別人就會圍上來。但我實在是忍不住了,我給了他兩個信封,他接下來的舉動我很驚訝,他吃力地擡起一隻手臂,把錢擋了回來,說,“這個錢,不該你給,該由政府來給。”這,是一個垂死病人說的話。#p#副標題#e#
“十年休養生息”
我們使用了社會支持評估量表、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和抑鬱量表給每位患者進行評分,發現廣西患者的抑鬱症狀遠高於河南(廣西92.9%的患者肯定有抑鬱症狀,而河南這一比例則爲53.3%),且廣西患者在朋友支持的得分亦高於河南,對他們來說,生存的、物質的援助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精神上、心理上和知識上的援助,這些病人因爲吸毒、賣淫得病,有道德和輿論上的壓力,不敢公開自己的病人身份,心理的陰影很大。
而河南,他們不說自己賣血,都說“獻血”,有個染病的村民告訴我,他前後獻的血,有整整一水缸,他們村最多的獻了三水缸!他們沒有道德上的負罪感,只會覺得冤屈和社會的不公。對他們來說,首先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先要讓他們和他們的後代,活下去,心理援助還在其次。所以我想,國家要系統地關懷艾滋病人,也該有個清晰的策略,按需施救。
定性分析中,我們感到當時艾滋病村患者的情緒不穩,並認爲如果患者的下一代得不到很好撫育的話,這一情緒不穩的底線就很容易被突破,我想呼籲在疫情嚴重地區實行“十年休養生息”,而不再是統一以“經濟建設爲中心”。#p#副標題#e#
“最有意義的學問”
我還提過一個“艾滋超限論” ,艾滋病已經超出了我們醫學的範疇,它是個全方位的問題,沒有哪個病能像艾滋病那樣,使社會發生如此重大轉變的——因爲艾滋病,我們的避孕套上了廣告;因爲艾滋病,我們給吸毒者髮針具、發美沙酮;因爲艾滋病我們得學會和感染者打交道、和性工作者打交道、和同性戀者打交道……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醫學的視野,我們需要在更寬闊的領域裏談論艾滋病。
我給研究生開設艾滋方面的課程,就是希望我的學生不要把艾滋病想得太簡單了,不要把發避孕套想得太簡單了。你發了,他用嗎?我可以很輕鬆地就提出二十個不用避孕套的理由,還有最徹底的一個理由就是避孕套顛覆愛情!艾滋病出現以後學醫的、學公共衛生的,不僅需要醫學的視野,還需要社會學的視野,人文的視野。
一次我帶一名學生下鄉,離開的時候,我對他說:這是我這輩子裏,做的最有意義的一個學問,抵得過我前二十年做的所有學問。
以前,我研究的學問都比較虛,呆在校園裏,發發論文,可是現在,真實的苦難就擺在我的面前,我的力量雖小,可我每做一點,就幫到他們一點。我並不崇高,但我有自己的信念。
話回到當初,我第一次進村,我前面說過,當地的衛生局長問我的感想,而我,已經連說話、連思維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有氣無力地回了他一句套話:“這個病,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組織、哪一個政府所能單獨應付的。”
這是一句太老套的套話了,但我現在還覺得,這是一句大實話。艾滋病需要有人振臂吶喊,也需要有人默默做事。你可以說你沒有錢,你可以說你沒有資源,但是!但是!你能說你沒有愛嗎?
高燕寧,46歲,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2002年起,他帶着復旦的研究課題深入艾滋病一線,成爲高校公開進入河南艾滋村進行研究的第一人。
他先後奔走河南、廣西兩省的幾十個村莊,接觸了上千名病人,做了數十例詳細的訪談。後來,高燕寧在研究生中首先開設艾滋病社會支持的課程,將中國的艾滋病救助拓展到了社會學的領域。
 拜託了冰箱第二期安賢珉《迷霧森林》菜譜完整版視頻教程
拜託了冰箱第二期安賢珉《迷霧森林》菜譜完整版視頻教程  電飯煲做蛋糕怎麼做 教你輕鬆做出獨特美味的蛋糕
電飯煲做蛋糕怎麼做 教你輕鬆做出獨特美味的蛋糕  多吃木瓜真能豐胸嗎 豐胸選什麼樣的木瓜
多吃木瓜真能豐胸嗎 豐胸選什麼樣的木瓜  羊排怎麼做好吃 羊排的家常做法讓你讚不絕口
羊排怎麼做好吃 羊排的家常做法讓你讚不絕口  怎麼吃才能越吃越瘦 這些低卡減肥餐一定要收藏起來
怎麼吃才能越吃越瘦 這些低卡減肥餐一定要收藏起來  自己在家怎麼煎牛排 輕鬆做出美味可口的牛排
自己在家怎麼煎牛排 輕鬆做出美味可口的牛排  傣族的飲食文化特點 傣族喃咪種類
傣族的飲食文化特點 傣族喃咪種類  嚐遍美食 “八大菜系”的代表菜品你知道多少?
嚐遍美食 “八大菜系”的代表菜品你知道多少?  與星座女最無緣的星座男
與星座女最無緣的星座男  金牛座的男生如何成功的吸引女生
金牛座的男生如何成功的吸引女生  星座裏的非常女人
星座裏的非常女人  雙魚座的男生女生的性格有什麼特點
雙魚座的男生女生的性格有什麼特點  最讓男人崩潰的5大星座老婆
最讓男人崩潰的5大星座老婆  這些女人讓男人不敢輕易出軌
這些女人讓男人不敢輕易出軌  12星座的壓歲錢應該怎麼花
12星座的壓歲錢應該怎麼花  男人眼中最完美的7種星座女
男人眼中最完美的7種星座女  男子接陌生短信回“你是誰” 銀行卡遭盜刷12次
男子接陌生短信回“你是誰” 銀行卡遭盜刷12次  武隆女子花15萬換100萬假鈔被騙僅得1箱冥幣
武隆女子花15萬換100萬假鈔被騙僅得1箱冥幣  房產可以過戶給未成年子女嗎?
房產可以過戶給未成年子女嗎?  沙發漆皮掉了怎樣修復 真皮沙發換皮翻新價格
沙發漆皮掉了怎樣修復 真皮沙發換皮翻新價格  南充公租房的申請條件-南充公租房買賣政策
南充公租房的申請條件-南充公租房買賣政策  上海公租房的申請流程和申請條件
上海公租房的申請流程和申請條件  網購需謹慎:央視揭四大新型網絡詐騙手段
網購需謹慎:央視揭四大新型網絡詐騙手段  柳州公租房怎麼申請?柳州公租房怎麼管理?
柳州公租房怎麼申請?柳州公租房怎麼管理?  日本定檔2023年2月17日,湯唯《分手的決心》
日本定檔2023年2月17日,湯唯《分手的決心》  玄彬×黃政民!電影《交涉》上演韓版“萬里歸途”
玄彬×黃政民!電影《交涉》上演韓版“萬里歸途”  國產媽媽,終於不在嫂子的戲裏死了
國產媽媽,終於不在嫂子的戲裏死了  劍俠情緣之刀劍決根據什麼改編 講述了什麼故事
劍俠情緣之刀劍決根據什麼改編 講述了什麼故事  喜歡你周冬雨演技被點贊 揭喜歡你周冬雨扮演什麼角色
喜歡你周冬雨演技被點贊 揭喜歡你周冬雨扮演什麼角色  奇蹟改名奇蹟笨小孩 這部電影講述了什麼故事
奇蹟改名奇蹟笨小孩 這部電影講述了什麼故事  韓國五部高分犯罪片,《恐怖直播》只能排名第三,你看過哪些?
韓國五部高分犯罪片,《恐怖直播》只能排名第三,你看過哪些?  曾頒錯獎?"雞毛秀"吉米·坎托爾將主持第95屆奧斯卡
曾頒錯獎?"雞毛秀"吉米·坎托爾將主持第95屆奧斯卡  時令保健:立秋未入秋 提防“秋老虎”
時令保健:立秋未入秋 提防“秋老虎”  九寨溝有了專業醫療廢物處置系統
九寨溝有了專業醫療廢物處置系統  健康充電5個要點 別把午睡變“誤睡”(圖)
健康充電5個要點 別把午睡變“誤睡”(圖)  青蔥
青蔥  大白菜
大白菜  鰳魚
鰳魚  盲人從事醫療按摩要考證 10月中旬全國統考資格證
盲人從事醫療按摩要考證 10月中旬全國統考資格證  盤點4種無能男人不值得你付出
盤點4種無能男人不值得你付出  測一測,你的人緣咋樣?
測一測,你的人緣咋樣?  測試:細節看你真性情
測試:細節看你真性情  性心理測試:從交通工具看你的性慾
性心理測試:從交通工具看你的性慾  從鞋子看你的升職空間有多大
從鞋子看你的升職空間有多大  你在職場中的魅力指數高嗎?
你在職場中的魅力指數高嗎?  測試:想知道你出軌的機率多大嗎?
測試:想知道你出軌的機率多大嗎?  從咖啡廳裏測出來你的交友觀
從咖啡廳裏測出來你的交友觀  從髮型找尋屬於你的姻緣
從髮型找尋屬於你的姻緣  畢業生應聘經典爆笑語錄
畢業生應聘經典爆笑語錄  爆笑童言趣語
爆笑童言趣語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果子裏的人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果子裏的人  女人千萬別學這些強人的彪悍睡姿
女人千萬別學這些強人的彪悍睡姿  搞笑鬼故事:夜晚飛來的豔遇
搞笑鬼故事:夜晚飛來的豔遇  初生嬰長成10歲女孩的紀錄片在網上瘋傳
初生嬰長成10歲女孩的紀錄片在網上瘋傳  經典100問腦筋急轉彎
經典100問腦筋急轉彎  公交乘客QQ表情圖,爆紅網絡
公交乘客QQ表情圖,爆紅網絡  不孕病因:抗透明帶免疫性不孕
不孕病因:抗透明帶免疫性不孕  夫妻提高性生活高潮有好處
夫妻提高性生活高潮有好處  男人你陪產了嗎?你是英雄嗎?
男人你陪產了嗎?你是英雄嗎?  “代孕”引發熱議 贊同者反對者各有各的理
“代孕”引發熱議 贊同者反對者各有各的理  子宮異位症引起女性不孕症的新療法
子宮異位症引起女性不孕症的新療法  不孕預防從少女做起
不孕預防從少女做起  中藥偏方對症治療不孕
中藥偏方對症治療不孕  女人乳房脹痛並非好事
女人乳房脹痛並非好事  快速無創治療細菌性前列腺炎
快速無創治療細菌性前列腺炎  男人最怕不“性”之“炎”
男人最怕不“性”之“炎”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臨牀症狀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臨牀症狀  教你認清前列腺炎的症狀
教你認清前列腺炎的症狀  前列腺在性生活中的作用
前列腺在性生活中的作用  慢性前列腺炎的診斷依據
慢性前列腺炎的診斷依據  前列腺 男性必知的六大危害
前列腺 男性必知的六大危害  “誰”來拯救我的前列腺?
“誰”來拯救我的前列腺?  預防子宮肌瘤 從月經不調出發
預防子宮肌瘤 從月經不調出發  走出宮頸糜爛的理解誤區
走出宮頸糜爛的理解誤區  淺談孕婦嘔吐的原因及改善
淺談孕婦嘔吐的原因及改善  多囊性卵巢不是病?
多囊性卵巢不是病?  囊卵巢引發“痘痘”的重要原因
囊卵巢引發“痘痘”的重要原因  房事不潔是盆腔炎致病因
房事不潔是盆腔炎致病因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預防與調養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預防與調養  五大引起盆腔炎的主要病因
五大引起盆腔炎的主要病因  小寶寶發燒了用退燒藥須謹慎
小寶寶發燒了用退燒藥須謹慎  飲食太精緻也會導致孩子便祕
飲食太精緻也會導致孩子便祕  寶寶支氣管炎的護理要點
寶寶支氣管炎的護理要點  家長當心,別在不經意間傷了孩子!
家長當心,別在不經意間傷了孩子!  嬰兒及寶寶心肺復甦的急救
嬰兒及寶寶心肺復甦的急救  小兒肺炎護理是關鍵!
小兒肺炎護理是關鍵!  冬季氣候寒冷 易誘發小兒肺炎
冬季氣候寒冷 易誘發小兒肺炎  小兒腹瀉需要注意的幾大方面?
小兒腹瀉需要注意的幾大方面?  骨質增生患者日常保健的八大事項
骨質增生患者日常保健的八大事項  如何護理小兒髖關節脫位?
如何護理小兒髖關節脫位?  氣溫高容易誘發頸椎病
氣溫高容易誘發頸椎病  該如何控制骨質增生?
該如何控制骨質增生?  關於肘關節前脫位的治療
關於肘關節前脫位的治療  解析一則頸椎病典型病例
解析一則頸椎病典型病例  爲什麼會腰肌勞損呢
爲什麼會腰肌勞損呢  給你介紹一種防治頸椎病運動處方
給你介紹一種防治頸椎病運動處方  乙肝孕婦如何預防傳染後代
乙肝孕婦如何預防傳染後代  中醫問診:“溼滯”引發的胃炎
中醫問診:“溼滯”引發的胃炎  防禦艾滋病 拒絕同性追求
防禦艾滋病 拒絕同性追求  家中護理肺炎孩子的基本方法
家中護理肺炎孩子的基本方法  什麼是流行性感冒的病原體?
什麼是流行性感冒的病原體?  感染乙肝 都是亂性惹的禍
感染乙肝 都是亂性惹的禍  治療肺炎喘嗽的五大處方
治療肺炎喘嗽的五大處方  肝癌併發肝硬化的內外治療手段
肝癌併發肝硬化的內外治療手段  推薦 什麼疾病看中醫最好?
推薦 什麼疾病看中醫最好?  老年人便祕的飲食調理方
老年人便祕的飲食調理方  中醫對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的分析
中醫對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的分析  中醫方劑 排毒養生兩不誤
中醫方劑 排毒養生兩不誤  藥膳薏仁 養生治病功效多
藥膳薏仁 養生治病功效多  秋季養生 要傳統更要科學
秋季養生 要傳統更要科學  腱鞘囊腫 可嘗試中醫鍼灸
腱鞘囊腫 可嘗試中醫鍼灸  女白領小心“凍"成內分泌失調
女白領小心“凍"成內分泌失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