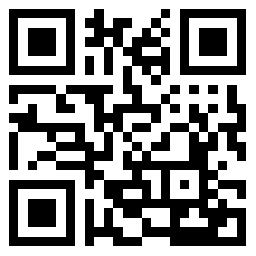
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隊裏,他工作老實勤快,僅僅花了半年時間,就被提拔爲隊長。每天下班後,他制服都顧不得換下,就趕到義工服務站做義工。
但這個常常穿着紅色背心、出現在公益活動現場的年輕人,卻在9月16日深圳保釣遊行中,表現出暴力的一面,參與砸車。
他砸壞的,是遊行當天停在深圳市委門口的一輛防暴車。7天之後,警方公佈了他與另外19個打砸者的大頭像,20個頭像佔滿了本地媒體《晶報》的整個頭版。自稱“扛不住事兒”的他一看就懵了,主動投案自首,隨即被依照尋釁滋事罪進行刑事拘留。
警方沒有透露他的真實姓名,稱他爲“李某”。
在深圳警方通緝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李某是第一個自首的。在看守所待了兩天之後,他所在保安隊的領導爲他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他特別熱心,又講義氣。”義工服務站負責人始終不能相信他成了通緝犯。這位負責人記得,這個小夥子第一次來到義工站,就主動忙前忙後,三五下就把一根壞掉的燈管修好了。
在義工站工作人員的印象中,長得濃眉大眼的他成天“笑吟吟的”,爲了幫忙搞公益活動,有時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周邊的孩子也喜歡這個穿制服的大哥哥,常常衝他喊“警察叔叔好”。
9月16日的早上,他卻沒有像平日那樣穿上那套深藍色的制服。因爲腸胃不適,他請假留在了宿舍裏。可沒過多久,他就忍不住走出宿舍,坐地鐵來到深圳華強北地鐵站。他聽同事說,當天將有參加保釣遊行的人在那兒集合。
地鐵站外,人山人海的場面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大街上多是與他年紀相仿的年輕人,他們扛着手寫的或打印的標語,扯着嗓子高喊口號。沒怎麼猶豫,他就加入到人羣中。
他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個村子裏。家中貧困,做代課教師的母親當時一個月收入僅有20元,父親耕種着家裏的4畝田地。初二那年,他作爲長子,輟學打工。
過去10多年裏,他到過山西、北京、天津、深圳等地。他當過汽修工,做過餐館的服務員,也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幹過。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始終幹着“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活兒”。
“不管別人怎麼看,有時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坐在深圳路邊的木椅上,29歲的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眼神始終躲閃着。
對遊行,他“沒什麼概念”。走在深圳的大馬路上,他起初感覺有點尷尬,“張不開嘴喊口號”,聽別人喊了好一會兒,才慢慢跟上。
往常這個時間,他正一個人站在約3平方米大的哨崗裏。他在深圳一家汽車4S店裏當保安,負責給每輛來訪的車發放停車證,“每天重複同樣的事”。
“乏味”是他評價日常生活時用得最多的詞。在6人一間的宿舍裏,他老坐不住,沒事兒就喜歡“沒有目的地逛馬路”。今年5月1日,他在街上閒逛時碰上義工站擺攤招義工,他問了一句“外地人也能報名嗎?”得到肯定的回覆後,馬上報了名。
端午節時,他給獨居老人義務包糉子。週末的時候,他到口岸維持秩序,給旅客指路,拎行李。他說參加這些活動,自己感到“單純的快樂”,讓生活“沒那麼枯燥”。
在深圳街頭,走在成千上萬的陌生人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很快,他喊口號就“越喊越來勁”。“抵制日貨!”“打倒日本人!”“收回釣魚島!”他用盡全身力氣使勁吼。過了一會兒,他甚至鼓足勇氣,在人羣中帶頭喊了幾次口號。
遊行的隊伍越發龐大,從不同方向涌來的人羣最終彙集到6車道的主幹道深南大道上。他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面,和30多個素未謀面的人一起擡着一面大國旗,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就齊刷刷地唱一遍國歌。
離開學校之後,他就沒怎麼唱過國歌,“連詞兒都忘記了”。但跟着大夥唱了幾回之後,“五音不全”的他就完全放開了,越唱越大聲。
“感覺愛國的激情被激發出來了。”他回憶說,那一刻,他感覺“挺暢快”。
前一段時間,他一直關注着釣魚島的新聞。他的宿舍裏沒有電視,也不能上網,他幾乎天天跑到大隊長的宿舍裏看電視,“越看越揪心”。
平日裏,他常常覺得“自己活得挺窩囊的”。“快30歲了,沒成家,又沒一技之長,可以說一無所有。”說起這些,他嘆了口氣,陷入了沉默。
去年夏天,他剛結束了一段失敗的婚姻。在老家的村子裏,離婚是件“很丟臉的事兒”。今年春節回家,他沒怎麼出門,大年初三剛過,就來到深圳打工。他說自己很喜歡這個“年輕,有活力”的打工城市。他的手機桌面,是他站在鄧小平巨幅宣傳畫前的單人照。
遊行的那一天,深圳的街頭讓這個年輕人頭腦發熱。他腦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頭就是“馬上把釣魚島給收回來”。
“如果當時發生戰爭,哪怕讓我當炮灰我也願意!”事後,他激動地對記者說。
想象中的“戰爭”並沒有發生,眼前迎來的,是人羣的騷亂。有人衝向了防暴車,有人暴躁地用腳亂踢,更有人爬上了車頂,拽着防暴車的水管。
他也跟着往前衝。他朝防暴車的側面亂踹了一會兒,眼看着“一點效果也沒有”,又撿起地上一根一米長的木棍,使勁撬防暴車的車門。堅硬的防暴車紋絲不動。他一下子掄起木棍,猛地揮向防暴車的後視鏡。
哐當一下,後視鏡被砸壞,玻璃碎了一地。
在狂熱的人羣中,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爲意味着什麼。他很快拋開了木棍,又重新加入到遊行的隊伍中。他更沒想到,馬路上的監控錄像已經將這一切拍攝下來。在隨後由警方截取並向全市發佈的頭像中,身穿黃色T恤的他表情有點兇惡。
如今,他不願意向記者回憶這些了。“我壓力真的很大。”說起砸車的那一幕,他眼睛一下子紅了,用手擠按着鼻樑,才極力忍住淚水。他不斷強調,自己“一輩子沒幹過違法的事兒”,當時是“一時衝動”。
在平日的生活裏,這個走南闖北的打工者極少衝動。在哨崗裏,他從來沒違反過“不能聽歌,不能看書,不能玩手機”的規定。“我不想讓領導覺得我不行。”他說。
離家打工的這些年來,這個“安分守己”的男人總感覺“身上的擔子很重”。他定期往家裏捎錢,有時幾百,有時幾千,但家裏的情況並未明顯好轉,磚瓦平房裏依舊空蕩蕩的。他的弟弟得了強直性脊髓炎。爲了多賺點錢,今年他父親到鄭州工地打工,母親到深圳一家餐館當服務員。
在母親眼裏,他“挺孝順”。她剛到深圳,兒子就給她買了一雙運動鞋,還帶着她去了一趟大梅沙和世界之窗。世界之窗的門票太貴,母子倆最終沒有進去,只在大門口拍了張照。
很少人知道,在心底深處,他有時會感慨“活在這個世界上沒什麼意義”。“我曾經想過死!然後把我的遺體和器官捐出去!”在QQ上,他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
在日常的工作裏,這個年輕人很少得到認可。在汽車4S店裏,他覺得自己“沒出息”,與那些賣車的銷售經理相比,“不是一個層面上的人”。“一個大老爺們做保安有什麼好的?”他甚至憤怒地質問自己。
做義工的經歷成了他最引以爲豪的事情。有一次,他在皇崗口岸幫一個來內地的香港人扛行李,對方遞給他一張500元的港幣,從來沒見過這麼大面值紙幣的他吃了一驚,但很快拒絕了。“我不能要,如果要了,就失去了做義工的意義。”
這件事情,他對母親,以及義工組組長都詳細說起過。至今,義工站的工作人員還會常常提及這件事,誇獎他。
但對於未來,他依舊感覺彷徨。他渴望再次成家,QQ簽名裏寫着“一直都在尋找真愛!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個她?”但他常常聽同事說,在深圳這個現實的都市裏,“追女孩都是要用錢去砸的”。每天站在哨崗裏,他也不時看見“四五十歲的男人帶着花季少女來”。每月拿着2300元工資的他一直沒有勇氣找對象。
走在深圳街頭,他似乎無所畏懼。他揮舞着從文具批發市場買來的一面國旗,看着一羣年輕人往味千拉麪店的玻璃上瘋狂地扔瓶子。警察出面制止,現場一片混亂。最終,他與扔瓶子的人被一起帶到了派出所。
錄口供時,他沒有提及自己曾經砸車。當天晚上回到宿舍裏,渾身痠疼,嗓子沙啞的他倒頭就睡着了。他當時還不太明白,參加“愛國遊行”的自己怎麼就被帶到了派出所。
直到在報紙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頭像,通緝“破壞公私財物的嫌疑人”,他才突然意識到,整個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個“犯罪分子”。早飯也沒吃,他就跑到派出所自首。
蹲在看守所裏,他感覺時間像停滯了一樣。每逮着一個人,他都要問一遍“我這種情況多久才能出去,一般怎樣判,判多久。”他擔心,他的人生從此就將“留下污點”。
離家打工之前,15歲的他最大理想是去當兵。但由於“家裏沒有關係”,他最終沒有如願。
後來,他特意去體驗了一次民兵訓練。訓練的最後,所有民兵一起扛着步槍去練習射擊。“那種感覺太好了,雄赳赳,氣昂昂的!”在夜色之中,他坐在木椅上向記者回憶起這些,眼神炯炯發亮。在這次訓練中,他獲得一張“優秀民兵獎狀”,這張薄紙,他至今保留在老家的房子裏。

 男子目睹父母火災中活活燒死後患上憂鬱症
男子目睹父母火災中活活燒死後患上憂鬱症  甲流疫苗接種方案:學生優先接種
甲流疫苗接種方案:學生優先接種  疫情籠罩,生活仍在繼續
疫情籠罩,生活仍在繼續  感冒藥吃過多易損害肝功能
感冒藥吃過多易損害肝功能  冰箱內發現感染可致死的新型細菌
冰箱內發現感染可致死的新型細菌  國產避孕套檢出有害滑石粉
國產避孕套檢出有害滑石粉  網上購藥需謹慎不可盲目
網上購藥需謹慎不可盲目  雞鴨瀝青脫毛“有毒”易患癌
雞鴨瀝青脫毛“有毒”易患癌  李湘年輕時的最美照片,膚白貌美(可謂少女感十足)
李湘年輕時的最美照片,膚白貌美(可謂少女感十足)  這是最成功的外來物種,卻很少被關注(池塘和湖泊中的噩夢)
這是最成功的外來物種,卻很少被關注(池塘和湖泊中的噩夢)  蔡卓宜個人簡介:參加過青春有你2(被網友稱之爲女海王)
蔡卓宜個人簡介:參加過青春有你2(被網友稱之爲女海王)  爲什麼男生有蘇聯情懷:實力強大(曾經是超級大國)
爲什麼男生有蘇聯情懷:實力強大(曾經是超級大國)  端午節的美好寓意是什麼?驅毒避邪祈福(傳承與弘揚非物質文化)
端午節的美好寓意是什麼?驅毒避邪祈福(傳承與弘揚非物質文化)  人造鑽石一年生產300萬克拉,80%來自中國河南!鑽石以後變白菜價
人造鑽石一年生產300萬克拉,80%來自中國河南!鑽石以後變白菜價  亞馬遜雨林中的恐怖河流,水溫超過九十度,動物進去就是自殺
亞馬遜雨林中的恐怖河流,水溫超過九十度,動物進去就是自殺  粉玫瑰不能隨便送人,容易產生誤會(送給愛人最好)
粉玫瑰不能隨便送人,容易產生誤會(送給愛人最好)  4·8南昌惡性殺人碎屍案:富二代與16歲女友連殺2人分屍
4·8南昌惡性殺人碎屍案:富二代與16歲女友連殺2人分屍  安吉拉·哈里斯:14歲患艾滋病,12年傳播100多人
安吉拉·哈里斯:14歲患艾滋病,12年傳播100多人  09年法航447空難原因:副駕駛不斷拉桿導致飛機失速墜毀
09年法航447空難原因:副駕駛不斷拉桿導致飛機失速墜毀  兵馬俑爲什麼不挖了 現代技術無法解決氧化問題(瞬間失去色彩)
兵馬俑爲什麼不挖了 現代技術無法解決氧化問題(瞬間失去色彩)  心情低落說說發朋友圈 主要是爲了舒緩心情得到安慰
心情低落說說發朋友圈 主要是爲了舒緩心情得到安慰  麥麩是什麼梗:音同“賣腐”(刻意與同性做出曖昧舉動)
麥麩是什麼梗:音同“賣腐”(刻意與同性做出曖昧舉動)  山東棗莊狼傷人事件:追趕兩小時纔將狼擊斃(咬死兩人)
山東棗莊狼傷人事件:追趕兩小時纔將狼擊斃(咬死兩人)  藍可兒事件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失蹤後酒店出現異常堵塞
藍可兒事件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失蹤後酒店出現異常堵塞  親愛的麻洋街小說原型介紹 麻洋街是真人真事嗎
親愛的麻洋街小說原型介紹 麻洋街是真人真事嗎  北京冬殘奧會賽程表出爐 六大項目的比賽規則是什麼
北京冬殘奧會賽程表出爐 六大項目的比賽規則是什麼  唐嫣短髮造型減齡美出天際 細數那些默默被唐嫣圈粉的理由
唐嫣短髮造型減齡美出天際 細數那些默默被唐嫣圈粉的理由  原來你還在這裏程錚和誰在一起 程錚堅定的愛讓人感動
原來你還在這裏程錚和誰在一起 程錚堅定的愛讓人感動  白敬亭成名前資料被扒 白敬亭是怎麼被發現出道的
白敬亭成名前資料被扒 白敬亭是怎麼被發現出道的  慶餘年範閒爲什麼去北齊 慶帝的心思只有兩個人看懂了
慶餘年範閒爲什麼去北齊 慶帝的心思只有兩個人看懂了  李沁和魏大勳分手了嗎 李沁鄧倫這麼甜魏大勳咋看
李沁和魏大勳分手了嗎 李沁鄧倫這麼甜魏大勳咋看  楊紫爸爸消防員父女神似 楊紫家庭背景全面曝光
楊紫爸爸消防員父女神似 楊紫家庭背景全面曝光  夢華錄朝代背景是宋朝嗎 官家和皇后是歷史上的誰
夢華錄朝代背景是宋朝嗎 官家和皇后是歷史上的誰  鳳囚凰容止歷史原型是誰 表面溫潤如玉內心卻腹黑深沉
鳳囚凰容止歷史原型是誰 表面溫潤如玉內心卻腹黑深沉  周生如故劉子行原型是誰 廣陵王歷史結局二十四歲就死了
周生如故劉子行原型是誰 廣陵王歷史結局二十四歲就死了  魯迅爲什麼討厭林徽因 曾撰文吐槽林徽因是無病呻吟
魯迅爲什麼討厭林徽因 曾撰文吐槽林徽因是無病呻吟  李存孝被五馬分屍是真的嗎 天生神力五匹馬都拉不動
李存孝被五馬分屍是真的嗎 天生神力五匹馬都拉不動  大明風華朱棣怎麼死的 永樂大帝死在班師回朝的途中
大明風華朱棣怎麼死的 永樂大帝死在班師回朝的途中  李世民宣武門之變到底有多慘烈 李淵爲什麼不救李建成
李世民宣武門之變到底有多慘烈 李淵爲什麼不救李建成  襄城公主叫什麼名字 李世民把襄城公主嫁給誰了
襄城公主叫什麼名字 李世民把襄城公主嫁給誰了  顏回殺妻的故事的寓意 若不是孔子顏回險些釀成大錯
顏回殺妻的故事的寓意 若不是孔子顏回險些釀成大錯  朱瞻基爲什麼叫蟋蟀天子 說一說朱瞻基鬥蟋蟀的故事
朱瞻基爲什麼叫蟋蟀天子 說一說朱瞻基鬥蟋蟀的故事  神話傳說中的姑獲鳥是什麼 姑獲鳥能預報災禍真假
神話傳說中的姑獲鳥是什麼 姑獲鳥能預報災禍真假  高枕無憂出自什麼典故 孟嘗君與馮諼的故事經過
高枕無憂出自什麼典故 孟嘗君與馮諼的故事經過  黑白無常生前的故事基情滿滿 原來冷麪陰差還能這麼感人
黑白無常生前的故事基情滿滿 原來冷麪陰差還能這麼感人  彌子瑕和衛靈公的故事 彌子瑕失寵後怎麼樣了
彌子瑕和衛靈公的故事 彌子瑕失寵後怎麼樣了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是真的嗎 司馬光砸缸救下的小孩是誰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是真的嗎 司馬光砸缸救下的小孩是誰  春節年獸的傳說和故事 春節哪些習俗跟年獸有關
春節年獸的傳說和故事 春節哪些習俗跟年獸有關  葡萄牙太陽神蹟是怎麼回事 太陽神蹟真僞性有待考證
葡萄牙太陽神蹟是怎麼回事 太陽神蹟真僞性有待考證  乾隆棺材移動怎麼回事 乾隆棺槨頂門嚇退盜墓賊
乾隆棺材移動怎麼回事 乾隆棺槨頂門嚇退盜墓賊  哪裏爆發過喪屍病毒 這些關於喪屍的傳聞你聽過嗎
哪裏爆發過喪屍病毒 這些關於喪屍的傳聞你聽過嗎  古代墓葬真的有各種機關嗎 後人的想象力可以有多豐富
古代墓葬真的有各種機關嗎 後人的想象力可以有多豐富  三豐百貨倒塌靈異事件 倖存者目擊到不可思議的現象
三豐百貨倒塌靈異事件 倖存者目擊到不可思議的現象  爲什麼人類害怕屍體:主要有四個原因
爲什麼人類害怕屍體:主要有四個原因  故宮爲什麼5點關門 難道故宮晚上真的會鬧鬼嗎
故宮爲什麼5點關門 難道故宮晚上真的會鬧鬼嗎  1971美國劫機事件真相如何 成爲美國四大懸案之一
1971美國劫機事件真相如何 成爲美國四大懸案之一  想不到,原來南海是這麼填島的!
想不到,原來南海是這麼填島的!  盤點全世界的主戰坦克【組圖】
盤點全世界的主戰坦克【組圖】  美國特種兵兼職拍色情片 女主角竟是自己老婆部隊領導都看過
美國特種兵兼職拍色情片 女主角竟是自己老婆部隊領導都看過  我國首顆量子衛星交付 美稱沉寂了一千年重回發明創新之巔
我國首顆量子衛星交付 美稱沉寂了一千年重回發明創新之巔  美軍10張最震撼人心的軍事攝影
美軍10張最震撼人心的軍事攝影  日本女兵婦科體檢圖片 裸體女兵體檢肛檢過程曝光
日本女兵婦科體檢圖片 裸體女兵體檢肛檢過程曝光  世界頂級熱點武器盤點 空警 500和合肥艦上榜
世界頂級熱點武器盤點 空警 500和合肥艦上榜  美軍不清純照片事件 受害人:分享女兵照已持續十幾年
美軍不清純照片事件 受害人:分享女兵照已持續十幾年 



